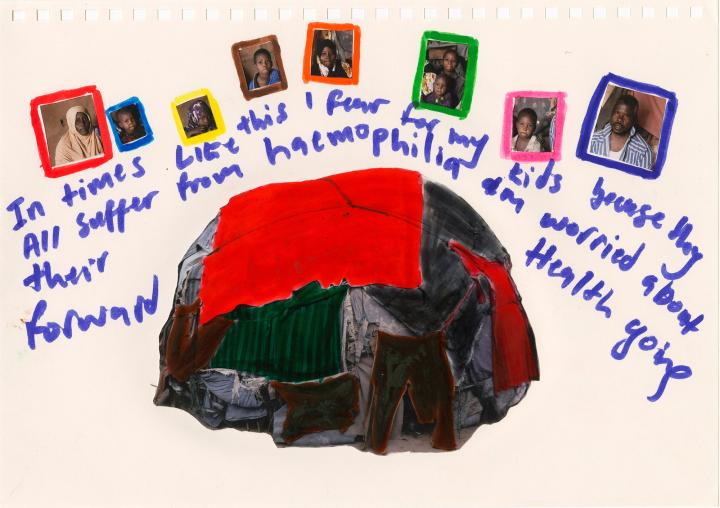宏都拉斯與墨西哥:追尋在道路盡頭的希望
數千個家庭為了逃離宏都拉斯的暴力與不安全,他們或者步行,或者搭乘火車、巴士,移動數千公里,拼命設法抵達美國。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被困在墨西哥,多是非常危險的城市,在那裡,他們成為綁架、攻擊、勒索的對象。出身墨西哥格雷羅州的攝影師雅耶爾·馬丁尼茲,花了數週時間與無國界醫生一同在墨西哥和宏都拉斯間往來,一路上遇見了這些甘冒極度風險,追尋在安全之地擁有更好生活夢想的人們。在他的記錄中,描述了這一路上他所遇見的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病患以及其他人。
科亞查科亞柯斯,墨西哥——北上

凱倫‧尤瑟琳,7歲,已經和媽媽及小妹妹旅行了十二天。在離開宏都拉斯約羅(Yoro)後,他們從墨西哥恰帕斯州塔帕丘拉市(Tapachula, Chiapas state)出發,一路走到韋拉克魯斯州科亞查科亞柯斯市(Coatzacoalcos, Veracruz state)。凱倫尤其擔心她的媽媽因為帶著年幼的妹妹而無法爬上北上的火車。墨西哥,2021。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噪音震耳欲聾。有那麼一會兒,我感到心臟在左耳快速跳動,一股震動慢慢從地面竄出,直到充滿我整個身體。我親眼目睹有人把一個硬幣丟到鐵軌上,八歲的宏都拉斯男孩亞西爾帶著一抹淘氣的微笑,彎腰撿起來遞給我。我撫摸這個幾秒前還是五十分硬幣的東西,因為與鋼鐵的撞擊仍顯得溫熱。我思索金屬與金屬間的壓力代表什麼——生活的壓力,不可避免的壓力、追尋的壓力,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壓力。
這個毀損的硬幣就像是我們在嘗試自我追尋的形象。是我們的暴力形象,是我們所經歷的暴力,是我們在人生進程中所經歷的軌跡。

3月23日當晚,科亞查科亞柯斯市有超過七百名中美洲人暫棲在鄰近鐵軌的這座橋下。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
拉米列茲一家人在橋下等待開往蒙特雷市(Monterrey)的火車。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天色越來越暗,又是另一個在鐵軌上結束的一天。黑暗籠罩我們,人們聚集起來生火,在夜裡保護彼此。由於疫情以及對新冠肺炎的恐懼,科亞查科亞柯斯市當地的難民中心已經關閉數月。亞西爾和他的父親威爾森已經被困在這裡數週,等待可以安全爬上火車的機會。他和許多其他家庭一樣—包括女人和小孩,全都在等待同一件事,等待火車停下來幾秒鐘,他們就都可以安全地上車。這是漫長的等待,而且耐性慢慢地耗盡了。同一天,一個女人在試圖爬上一輛行進的火車時掉了下來,她掉落的畫面讓所有人心驚膽跳。即使在震耳欲聾的火車行進聲之下,她的尖叫聲仍清晰可聞。幸運的是,她落在離鐵軌稍遠的地方,並迅速爬起來,立刻沿著鐵軌朝遠方的地平線狂奔——不論往哪裡去,唯一確定的是,這些軌道指引著她的方向。



3月24日,尚巴拉諾一家人仍在橋下等待。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

我向亞西爾和其他孩子告別,跟無國界醫生媒體專員葉卡回到飯店。在離開前我走到火堆邊感覺它的熱度,感覺和那裡的人更靠近一點。在這座橋下,鐵軌旁,時間以不同的方式運行。在這些夢想碰撞以及離開家鄉的人的聲音所在匯集的空間,時間總是以不同的方式運行。


第二天早上,我們出發前往希格拉斯鎮,這是一個位於科亞查科亞柯斯市北邊的社區,是往北方的旅程中停留的小地方。我們走在鐵軌上,我停下來,跟兩個睡在火車車廂下面的男人談話。他們一路上幾乎都是用走的,腳上傷痕累累。其中一人突然指著遠方的一個車廂,有個家庭正在拍攝一部呼喚某人搭乘「野獸」的影片(「野獸」是許多人對開往美國貨運火車的稱呼,移民和尋求庇護者經常嘗試攀爬上去往北走)。我走向他們,爬到車廂上。他們來自宏都拉斯,已經旅行12天了。這群人中年紀最小的是7歲的凱倫,她的相貌獨特,彷彿在過去幾天內已經體會了數年的人生。她的頭髮在吹過的風中飛舞,讓畫面帶著魔幻的氛圍,彷彿她的身體離開了地面,漂浮在那鐵板上。我走向她,拍了張照片,車廂開始移動,我們落回了令人窒息的現實。結果火車並沒有開走,只是車廂調動而已。凱倫告訴無國界醫生的醫師,她很擔心自己的母親和妹妹,她想照顧她們,很擔心媽媽帶著年幼的妹妹無法順利攀上火車,這樣她們就會永遠分開了。



3月25日,一位父親協助女兒爬上一列科亞查科亞柯斯市的火車。墨西哥,2021。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

我從鐵道回來的路上,遇見艾德加和他的家人。他們早上成功搭上火車,但只到達希格拉斯鎮。他們在一座頹圮的小屋中休息,生火的痕跡仍然清晰可見。幾天前,他們還很樂觀,但現在他們的臉色不一樣了——他們的眼中有著恐懼與不確定。艾德加看著火車所在的地平線,上次他試圖穿越時,在沙漠中迷路了,漫無目標地走著。他告訴我他像嬰兒一般哭泣,覺得一切都完了,他要在沙漠中死掉了。邊境管制官找到他們,對他來說,那是重生的機會,他的救贖。他以為自己永遠都不會再度嘗試了,然而他現在在這裡,再一次,追尋在德州的新生活。

移民稱為「野獸」的火車奔馳於鄉間。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這個旅程的艱難之處在於讓自己無聲,在風景間隱沒,像拋棄一片片拼圖般把自己一點一點地遺落在身後,然後你看著鏡子,再也認不出自己,在時間、塵土與寒冷的糾結中失去了自己。
今天是我們在鐵道的最後一日,我們在破曉前抵達,許多人走來走去,比黃昏時還多得多。我遇見安荷和他的家人,並且跟他的父親交談。多年前他住在蒙特雷市,那是他們想去的地方,最小的孩子是墨西哥人,她在這裡出生,今天是她的生日。葉卡跑進店裡,帶著一個企鵝杯子蛋糕回來。我們拿火柴當作蠟燭,一起為德芙琳唱生日快樂歌,她要兩歲了。她的父親眼中帶淚,微笑地看著她。快樂的孩子們吃掉一塊蛋糕開始玩耍。背景的一片綠牆亮了起來,安荷開始擺弄他在牆上的影子,這個景象讓我覺得,區隔我們的是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的恐懼,我們對自己是什麼、可以是什麼、我們對未知和對他者的投射。
幾個小時過去,該走了。我向大家告別,看到安荷從遠方朝我跑來。他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說他會想念我。我起了雞皮疙瘩,告訴他要堅強,永遠不要停止夢想,把這段旅程想像成一場遊戲,一場即將結束的惡夢。
我的指路明燈引領我南下,到他的土地,我們的土地,試著去瞭解為何一個人會離開,為什麼我們的孩子不再屬於那裡。

安荷‧亞歷西斯‧拉米雷茲‧梅吉亞,9歲,三月25日在科亞查科亞柯斯市的橋下玩耍。在離開宏都拉斯科馬亞瓜市後,他和他的家人已經旅行了16天,其中有14天仰賴步行。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宏都拉斯—終身印記
我所聽說的宏都拉斯,是我在鐵道上遇見那些家庭的故事,他們來自洛羅(Lloro)、科馬亞瓜(Comayagua)、聖佩德羅(San Pedro)、桑布拉諾(Zambrano)、聖塔巴巴拉(Santa Bárbara)。他們都說自己在那些土地上沒有留下任何東西。那就是他們離開的原因,他們失去了一切。

2021年4月8日, 2020 年颶風對班德拉斯村造成的影響仍然可見,包括洪水。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從空中鳥瞰,這裡就像個叢林天堂,植被鬱鬱蔥蔥。我著陸時感覺如此熟悉,彷彿身在恰帕斯或格雷羅的柯斯塔奇卡(墨西哥)的某處。一切都這麼地親切,甚至包括好幾處被暴力滲透之地的氛圍。喬洛馬街區的牆幾乎和阿卡普科市拉斯克魯塞斯相同,有著時間、塵土、人們血汗的印記。

2020的颶風摧毀了科爾特斯州聖佩德羅蘇拉市(San Pedro Sula)普拉內塔(La Planeta)的鄰近地區。宏都拉斯,2021年。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當你走路或移動時,你的潛意識會感覺到有人正在看著你——你看不見他們的臉,說不出他們的名字,就像是被遺忘的神明,像是被燒毀的土地一般。

一名性暴力倖存者攝於宏都拉斯的喬洛馬市(Choloma)。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Y. M.從八歲開始就遭到家人虐待,虐待造成一種空虛感,讓她強迫性地想以越軌行為填滿這個空虛,她迷失自我,她在街頭迷失。她的孩子給了她活下去、戰鬥的理由,讓她慢慢放下了情緒,卸去家庭留給她的印記,蛻變並從中學會寬恕並找到新視野。她用在田間工作的照片來代表自己。從照片中看不出來,但她其實懷孕了。此刻她感到完整,擁有活下去和承受任何事的力量。
當N.V.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她的空間、身體、靈魂的保護被擊碎的回憶,她嘆了口氣。想像看著那些你以為會保護自己的人的雙眼時,你看到的是施虐者的臉龐是什麼感覺。她告訴我們,當你經歷過那些,你會失去生存的意志,會感到內疚且骯髒。但她將之拋諸腦後,現在她看到了即將到來的獨立。她選擇了一張與她的女兒、護士合拍的照片,她看起來安詳、明亮,房間裡充滿和平的氛圍。
羅瑞娜非常緊張,右腳不斷拍打地板,呼吸也很沉重。當她開始講述她的故事時,她的聲音變得破碎,淚水從臉頰上滾落,接著她沉默了。從她的呼吸聲,可以感受到她內心是如何顫抖。塞西遞給她一張衛生紙,握住她的手。羅瑞娜擦乾眼淚,用濡濕的衛生紙包住左手食指。在那一刻,畫面投射出過去、她感受到的炎熱、飢餓、被摧毀的風景、荒涼的家園、人們拚命尋找安全的地方。這些畫面在我腦海中閃現,與夜晚的寂靜形成強烈對比,被鳥鳴聲打斷。

A.E.A.,34歲,性暴力倖存者。她站在位於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新首都附近的家中。宏都拉斯,2021年。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羅瑞娜的聲音慢慢平靜下來,我們注意到已經是晚上了。她告訴我們她的安全空間,能讓她感覺平靜的地方,是海邊,在那裡她只看到月光,感覺腳上的沙。
她決定將自己的故事記錄在皮膚上,透過圖像分享她的經歷。她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製作符號。我記得的是一個蒲公英的圖案。她告訴我們這種花是如何地脆弱,但不論被風吹到哪裡,都能開花。
格雷羅,墨西哥—沒有出口

格雷羅州(Guerrero)埃爾佩斯卡多村(El Pescado )缺電,只有配備太陽能板的房屋才有供電。墨西哥,2021年。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我們花了十二個小時才到達埃爾佩斯卡多村(El Pescado)。這是一段充滿風沙的漫長旅程,有時能見度幾乎為零,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和時間。要在山嶺間行走,你必須了解這個地區,我們以嚴峻的方法學到這件事:我們走了一條小路,在裡頭迷路了兩個鐘頭。當這條路變成死路時,我們意識到自己迷路了。我們不得不回頭詢問前往埃爾佩斯卡多村的路線。天色越來越暗,而我們還沒到達。我們以為會在下午五點左右抵達——那時是晚上八點二十分。葉卡很緊張。卡車上的每個人都知道,在這些道路上夜間行駛是不安全的。 在這些偏遠的地方,國家是不存在的。社區有自己的律法;他們築起自己的防護牆,保衛自己不受毒販攻擊、反對同業聯盟,不與他人鬥爭。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想拜訪社區。幾個月前,一個武裝團體攻擊這裡的人,他們被迫搬遷。 這場戰爭是為了土地,為了鋸木廠。這裡已經有一段時間不種罌粟了。
我們終於抵達埃爾佩斯卡多村,並在學校搭起了帳篷。社區裡沒有電,那天晚上月色美麗,照耀山嶺。社區給我們手工製作的玉米餅、黑豆、米飯和雞肉當作晚餐。在長途跋涉後,這是一頓美好的晚餐。

4月28日,18歲的瑪麗貝爾‧穆吉卡和她的兩歲兒子加布里爾在格雷羅地區埃爾佩斯卡多村的家中。墨西哥,2021年。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第二天,社區的人開始到達無國界醫生的營地。他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醫療服務了。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和人們的臉上感受到不確定性。到處都有軍隊、國民警衛隊和州警察。你可以感覺到表面的平靜即將消失,格雷羅州表面的平靜。

由於格雷羅州普遍存在暴力和組織犯罪,埃爾佩斯卡多這個小村莊的家園已遭拋棄。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


哈維耶‧赫南德茲是埃爾佩斯卡多村的一位社區領袖。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我們在採訪哈維耶之前等待。他告訴我們武裝人員何時抵達、不得不拋下一切離開的家庭、他們在這裡所面對的困難和社會的困境。他告訴我們,他們決定留下來為他們擁有的東西而戰,為他們的土地和人民而戰。
夜幕降臨,人們慢慢散去回家,有些人搭乘「野獸」可能要花上一個半小時。
醫生們帶來他們在健康中心用來照明的燈。家庭等待諮詢,醫囑是在各種克難的光源下開立。我記憶中揮之不去的畫面是一位母親帶著她的女兒在黑暗中走路回家,只用手機照亮他們的路,一條他們在夜晚獨自行走的道路。只有手機照亮他們的路程,一條他們會在晚上獨自走的路。是在那些狀況下會把你推到極限的路,這是一種信仰行為。

阿洛堯家族得在黑暗中行走兩個鐘頭才能到家,因為害怕組織犯罪,他們必須離開。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隔天我們離開埃爾佩斯卡多村,但在那之前我們採訪了一個家庭。他們已經離開社區,他們遭到恐嚇並且十分害怕,妻子同意和我們談談。我們正步行到一個親戚家,在路上,她遇到另一個女人,她變得非常緊張。她告訴我們,整個社區都受到監視,她感到不安全。她改變了同意拍照的想法,但願意給我們一個簡短的說明。她說得很簡短且斷斷續續,話語並不順暢;沉默和她的聲音裡充滿恐懼,以及對她和一家人生活的不確定性。
下午,我們移往埃爾杜蘭諾(El Durazno)社區。當我們看到一群武裝人員朝我們走來,有那麼一剎那我們感到緊張。他們都有長槍和自動武器,鮑爾(無國界醫生的一名工作人員)去面對他們。他們很不高興,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帶補給去給埃爾佩斯卡多村;他們跟那個社區有衝突。那是一個緊張的時刻,但鮑爾告訴他們可以跳上我們的貨車看看裡面有什麼。他們讓我們走了,幾分鐘後,一位社區當局的官員來了,為我們遭到的對待道歉。我們終於去吃飯,那天下午稍晚之後我們採訪了他。他告訴我們脈絡,種植作物的需求、他們為什麼要保衛自己的土地,以及為什麼那裡會有衝突。鮑爾問起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其中一位武裝人員開始說話:「衝突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希望衝突早日到來。」夜幕降臨,風吹過松樹, 霧氣籠罩著高山,連空氣都令人感覺緊張。
第二天,我們離開了山脈前往芝華塔尼歐市(Zihuatanejo)。那是漫長的日子,讓你感覺怪異,充滿了即將發生的不確定性,淺眠讓你更貼近地球,感覺脆弱,感覺像是水從手中溢出。

亞曼依蘭妮‧穆希卡,7歲,她在埃爾佩斯卡多村的家中拭淚,由於組織犯罪緣故,這個村莊的家庭都缺乏醫療服務、安全、以及經濟發展的機會,有許多被迫離開。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幾天前我收到葉卡的訊息,那是一段婦女哭泣著向當局尋求協助的影片。那些[在我們訪問埃爾佩斯卡多時]接受過醫療照顧的婦女,現在在同一個醫療中心為她們和孩子的生命哭求。你可以聽到遠處的槍聲,可以感覺到房間裡如何充滿恐懼,聲音是如何崩潰。這些聲音來自另一個時間,來自女孩、男孩、女人、母親、祖母。 他們都變成同一個聲音,像一顆跳動的心臟。這些土地被遺棄、支解、連根拔起、貧瘠。

組織犯罪集團為了能夠控制木材而想佔領森林,這是人們被迫離開這些土地的原因之一。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灰塵和泥土的氣味就和喬洛馬以及科亞查科亞柯斯一樣,那是我們這個時代人的氣味。
塔毛利帕斯,墨西哥—路上的血跡
我一直認為邊境城市是暴力的,自然的力量和人衝突,和我們思考和理解生活的方式衝突,人與人發生衝突,與我們所定義的現實發生衝突。


塔毛利帕斯州擁有這些可見的印記——在她的地理、空間、人民的靈性中。在這裡,夢想不僅只是試探,他們燃燒,血流至死。
空間似乎因為被哀悼的聲音籠罩而顯得沉默、震驚。


這是我們[在雷諾薩的第一天,我們和無國界醫生媒體專員塞吉奧一起去了一個避難所。我們採訪了一個逃離祖國的宏都拉斯家庭,他們害怕被自己的血親和家人殺死。 女人不斷流淚,抱著她的丈夫。她再也不認識自己——離開宏都拉斯後,她和她的家人就不一樣了。時間和現實改變了他們,他們所經歷的改變了他們。看著他們互相擁抱、彼此凝視,我起了雞皮疙瘩。他們跟離開宏都拉斯時不同,也跟昨日不同,但這個可怕的現實也讓他們沒有沉淪,他們變得更加緊密。

辛蒂‧卡賽列斯,28歲,卡羅斯‧羅伯托‧圖內茲,27歲,他們來自宏都拉斯,目前留在雷諾薩,同時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又是另外一天,今天我們遇到一個跨國家庭:父親是海地人,母親是宏都拉斯人,最小的孩子是墨西哥人。他們在恰帕斯州相遇,這條路將他們帶到了墨西哥北部。 當我們到達附近,一個墨西哥女人帶著敵意問我為什麼要拍照。我解釋我們正在做的工作,然後進到屋子裡。一個小時後她進來,態度迥然不同。她開始威脅羞辱我們,我們只能離開。那個房子很大,幾個海地家庭一起合住。 那部分街區被毒販控制。
我們離開了那棟房子,國家的遺棄對我來說變得更為明顯。第二天黎明前,我們抵達雷諾薩的營地,這個不斷擴大的營地現在已經有大約 500 人。所有人都帶著微小的希望等待機會。前一天試圖越過邊境的人待在一個亭子的樓梯上。他們的衣服又髒又濕,鞋子上都是泥巴。他們身心俱疲筋疲力盡。我試著跟他們交談,但不能幫他們拍照。我的記憶回來了,我的身體記憶沉重,肌肉緊繃。我無法入睡。

來自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墨西哥,大約有500人擁擠地住在雷諾薩市中心的新營地。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我們聽到令人心碎的故事,歷史重演,迫害者似乎是相同的,有人捅刀別人,反映的是我們自己,我們最深的夢想或恐懼。

49 歲的弗雷迪‧阿爾貝托‧帕邦在他的母親和兄弟去世後離開了委內瑞拉。他正在為自己和其他家人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沒有人能夠繼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了,她已經被我們的野心和暗黑慾望焚燬。
我帶著死亡、危險的印象離開塔毛利帕斯——我看到一個女人被一個男人輾過,他非但沒有幫助她,還想把她丟棄路邊,繞過她,把她扔在人行道上,彷彿她只是一件東西。

路易莎‧科圖,33歲,在收到死亡威脅並失去兩位家人後離開了她的國家。她現在住在雷諾薩的一個營地。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我記得有人告訴過我們,晚上有些婦女和兒童會從營地消失,就在眾人的眼前,在每個人的恐懼之中。
那個女人被撞倒的影像仍然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她臉上帶著迷失、茫然的神情,彷彿死了一般。這個影像如同她在人行道上的血一般完全浸透了我。
這只是一場旅程,為了適應力強的人類,為了所謂的為生命而戰,為了所有的團結之聲,為了我們存在之歌永恆燃燒。

格蘭德河流經馬塔莫羅斯。
© Yael Martínez / Magnum 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