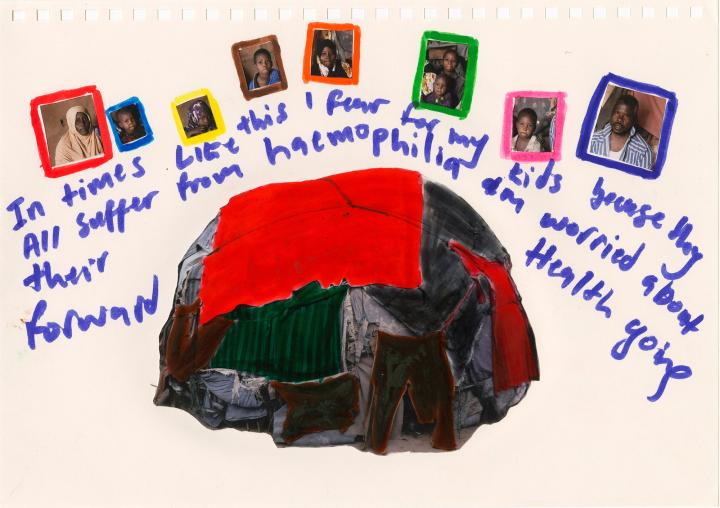伊土里,裂隙中的微光

瑪紐希(Manyotsi),32歲,懷裡抱著她六個月大的孩子。這孩子是因遭強暴而懷上的,儘管如此她說依然愛這孩子,因為孩子是無辜的。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自從 2017 年暴力頻仍肆虐以來,一百多萬人流離失所。各種燒殺劫奪和暴行迫使許多人不得不離開家園,前往勉強安全一些的收容營中避難。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們還必須面對各種傳染病、因衛生條件不足造成的諸多感染、以及性暴力問題。他們仰賴救濟維繫生存,但駐地的救援組織相當少。攝影師紐夏·塔瓦柯利安(Newsha Tavakolian) 前往伊土里記錄一些流離婦女的現況和她們在每日生活中遭遇的暴力。
前往德羅德羅的途中
"再過半個小時,就是春分了,也是波斯的新年——諾魯茲節。人們說太陽位於天球赤道上春分點的時候,你在做什麼,將決定接下來這一年的運勢。我受無國界醫生組織專案委託,現正乘車前往德羅德羅,進行一個針對性暴力的報導計畫。"
那些與我們交錯的來往車輛中,人們戴著簡易的蓋頭以遮蔽因車行揚起的飛灰煙塵。我們行駛的這條路,如蛇行一般蜿蜒曲折,相當泥濘,輪胎深陷其中。
我們再次在一個檢查哨停下,我迴避那些非政府軍的武裝集團士兵們布滿血絲的目光。這些士兵穿著軍裝、手持武器,其中有些不過是孩子。有隻手以那長有老繭的手指背,順著我的手臂肌肉滑下,我則眼盯著那穿透擋風玻璃唯一一道水平裂隙的光。豬隻的嚎叫聲不絕於耳。我要司機加速,快快將這一切甩在後面。前有岔路,一條通往蘭杜人(Lendu)的社區,而我們則右轉往德羅德羅去;當地收容了數千名流離失所的希瑪族人(Hema)。在泥牆草屋之外,生活繼續著。映入眼中一望無際的唯一影像,是收成的和晾曬中的木薯。

在德羅德羅,有個名為祖雅(Tsuya)的簡陋收容營,已設置多年,約住有兩萬人。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
德羅德羅村莊三個少年站在自家草屋後方的一片田地裡。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我們抵達德羅德羅村莊,雖然還要過幾日才是禮拜天彌撒,但有一群人聚集在一個受難耶穌的大十字架周圍。我們因為必須趕往德羅德羅醫院,不能停下來訪問;已預先安排了我去採訪那些受營養不良之苦的母親和她們年幼的孩子。

在德羅德羅主要道路旁立有一個十字架,每日吸引越來越多的人群聚集。原因是這尊耶穌雕像斷掉的腳部會流血,真是一種神蹟。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蚊帳裡,嬰孩們因病痛呻吟哭鬧著。在一位醫師的協助下,我與一個沒有笑容的年輕女孩見面,我請她擔任我的助理,在我拍攝期間幫忙打光。在建築物外面,有一些親屬聚集,用他們僅存的當地作物——木薯、香蕉和鳳梨,開始為他們住院的家人備餐。

由於缺乏食物,許多婦女和孩子都嚴重營養不良。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儘管剛果民主共和國蘊含豐富的天然資源——石油、鑽石、鈷和尤其著名的黃金,但絕大多數的剛果人民卻極度貧困。數百萬人民流離失所,且每日暴露在身體的暴力和性暴力的危險下。逞凶施暴的是那些民兵,這些人的惡行不受懲治更使得百姓(尤其是男人們)有樣學樣,而主要受害者都是婦女和孩童。


在剛果東北部伊土里地區,從事農耕的蘭杜人和從事畜牧的希瑪人兩個族群之間的衝突格外嚴重。有三名受傷的蘭杜年輕人被無國界醫生帶到希瑪人的收容營治療時,希瑪族人群情激憤,很快地包圍了無國界醫生的車子,他們威脅醫療團隊不得在營中治療這些敵對部落之人。最終,無國界醫生只能將這三名傷者送往另一所醫院,以避免衝突。


有一些女性社運人士提供協助給遭性侵者,成立了「性暴力受害婦女聯合會」(SFVS)。會長茱絲汀媽媽(Justine)告訴我,性暴力的常態化,並非僅是剛果政治局勢不穩造成的;她解釋說當地的社會文化也助長了將女性貶抑為物件。
的確,過去曾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傳統習俗,鼓勵男人把他們喜歡的伴侶帶回家關起來,意即綁架她,當然沒有徵求她的同意,然後再跟她的家人談是否聯姻。茱絲汀媽媽說,現如今狀況還是很複雜,因為有一些偏差的信仰和迷信將性暴力正當化,甚至還有某些人相信跟處女發生性行為能夠治癒愛滋病。

從無國界醫生的車內拍攝,德羅德羅的路景。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
德羅德羅的景色。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無止盡的衝突

在德羅德羅拍攝的三名剛果男人。由於失業、沒有謀生方法,再加上一種極度貶低女性的社會文化,連帶導致對婦女施暴成為某種常態。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剛果曾被比利時王室殖民,開採其天然資源;當時稱為剛果自由邦,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éopold II)的私人土地。之後於1908年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1960年,剛果人頻頻抗爭,最終揭竿而起,成就了國家獨立。但是這並不意味衝突結束:混亂、政變、叛亂,層出不窮。
剛果第一位合法民選出的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被暗殺,使得組建一個有能力為剛果人民謀福利的中央政府之可能性幻滅;或許,一個中央政府能在某程度上避免往後數十年的剛果內戰。繼盧蒙巴之後任總理的蒙博托.塞塞.塞科 (Mobutu Sese Seko),在美國和法國政府的協助下,獨裁專政長達三十年。由於鄰國盧安達軍事入侵,其獨裁政權終於被叛軍領袖洛朗-德西列.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推翻,而這也掀起了剛果第一次內戰,以及後續的其他衝突。


第一次剛果內戰(1996 – 1997),也被稱為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戰,起初是一場內戰,但很快地變成一場國際衝突,牽涉蘇丹、烏干達和安哥拉,並且還牽涉西方勢力,尤其是法國和美國。第二次剛果戰爭始於 1998 年 8 月,直到 2003 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過渡政府掌權時,才正式結束。儘管當時簽署了一份和平協議,但暴力事件仍在境內各地發生,特別是在剛果東部,其中包含伊土里地區。雖然伊土里的衝突早在 1970 年代就已展開,暴力程度卻在 1999 年與 2003 年間達到高峰。
時至今日,緊張情勢與武裝衝突均未曾稍停。
攻擊成為唯一的選項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
我遇見吉賽兒(Giselle)時,夕陽美得極致。她是個十六歲的大女孩,短頭髮,穿著一件米白色襯衫,一件長裙,套著一雙上面印有 VIP 字樣的塑膠拖鞋。她說,母親在生下她最小的弟弟後,發瘋而後失蹤了。2018年的某個夜裡,叛軍襲擊他們的村莊,殺了所有人,她的父親也死了,吉賽兒和她八個弟弟妹妹是部分倖存的生還者,所以她自此挑起照顧家裡的責任。兩個月前,某日和另外五位婦女一起去取水時,吉賽兒因為挑著沉重的水桶走得較慢,落在隊伍後面。登時有三個持槍的男人抓住她,逼她脫衣,他們性侵她時拿槍頂著她的頭,不讓她叫喊。他們一個又一個的輪姦她,另兩個就在路旁把風。
全身瘀青,驚恐未定,吉賽兒努力讓自己站起來,走剩下的路。一個騎機車路過的人看見她的痛苦和無助,載她到營區。回到營區後,一位年長的婦女注意到她的異樣,在聽她敘述遭遇後,鼓勵她前往健康中心求助。在遭性侵後好長一段時間,吉賽兒都無法好好的站立或好好的走路,但她沒有別的選擇,她必須繼續照顧年幼的弟妹。吉賽兒告訴我,在被三個男人強暴後(那還是她的初次性經驗),她再也不想和男人有任何瓜葛,她發誓永不結婚,發誓要繼續學業好有能力照顧弟妹,並且幫助她族裡的婦女。她流露出憂傷和莫大的孤獨,跟我訴說失去雙親她感到好無力,她每天都好想念母親。
我在村裡走走看看,驚歎於四周的美景。這裡的天空看來如此寬闊,同時又是那麼貼近大地,彷彿只要伸出手就能抓住那像棉花糖般的雲朵。我再一次走到那個大十字架附近,人群始終圍繞著十字架,越聚越多。我好奇人們為何不斷聚集於此,問了人,回答說耶穌像的右腳處斷了,某種深紅色液體從裂口流下來。群眾似乎相信耶穌像在流血。我無法在流血的耶穌像附近久留,因為必須前往健康中心。
在健康中心
我在德羅德羅的健康中心遇到尚-克勞醫師(Jean-Claude)。這個健康中心原先是由「免於飢餓行動組織」(ACF)支援,盡所有可能地照護著許多婦女和孩童。不久前一些希瑪族人放火燒了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基地,焚毀他們的車輛,並且強迫那些工作人員連同「聯合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維穩任務」(MONUSCO)的援助全都撤離。今日,「免於飢餓行動組織」已不在這個地區工作,這意味著那些來到健康中心的婦女和年輕女子已無法獲得免費的照護,而那正是她們迫切需要的。


我問尚-克勞醫生是否能用英文溝通,他回答說在某程度上可以。我問他在哪裡可以找到為性暴力受害者服務之人,他說他本身十年來都在照顧這些婦女,並補充說其中許多人是被她們認識的男人性侵,不見得都是遭民兵強暴,而是她們自己的家人、或是社區裡的其他男性。
在這些收容營裡,沒有什麼事可做。孩子們多半衣不蔽體,年紀稍長的都幫著家人在田裡耕種,或是去提水。不論是取水、食物、準備柴火,或是田地裡的勞作,擔負大部分責任的,都是女性。大多數的性侵事件都發生在她們為了確保家庭生計而外出的途中。

幾個年輕女孩在去取水的必經道路上讓我拍照。這條路通往那些住在羅霍收容營以及附近居民唯一能夠取水的地點。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尚-克勞醫生告訴我,性暴力實際上是一項戰爭武器,一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同時那些男人們也將侵犯與凌辱女性身體作為他們宣洩自己挫敗沮喪的管道。「可是為什麼?醫生,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男人們失業、失去生計能力,感到挫敗而無力,侵犯女性於是成為他們宣示某種能力/權力的方法。我想到恩札樂(Nzale),她只因為拿不出伍佰剛果法郎(不到一美金)就遭到性侵。
反差是如此懸殊:這片土地豐饒、肥沃、茂盛生長著各種熱帶作物和奇麗花朵,但這片土地卻也孕育不可理喻的暴力。尚-克勞醫師承諾會替我連繫當地一個協助性暴力受害者的人道關懷組織後,我離開了健康中心。市場上有這麼多的婦女,身上揹著綁著幼小的嬰孩,來來往往、備置食物,而周遭的男人卻無所事事。剛果就像這些美麗女性的命運,一再地被強暴,讓每個入侵者拿走一片衣裳、奪走身體的一部分。


我從一群穿著學校制服白衣藍裙的女孩前面經過,她們和抱著課本的男同學們肩並肩一起走在黝綠樹林旁。那是季風帶來雨水的季節,油亮的香蕉葉上還滴著雨水,我無法克制自己去想,男孩中誰會對這些女孩施暴嗎?若真有施暴者,那誰會保護她們呢?
塞吉(Serge)是心理師,他主持一項新的醫療計畫,以改善當地性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為目標。至今協助這些女性已有一年,他說,這些婦女最常見的兩種情緒是羞恥感和罪惡感,而對於遭到性暴力傷害的經驗還有兩個普遍的反應:精神全然崩潰、或是否認以求遺忘。
我想起當我問神父為何這些婦女和女孩都等著要告解時,神父告訴我的話。「神父,她們為什麼在這裡?她們如此迫切地想要告解的是什麼?」神父回答我:「有些事積壓在她們心上,她們無人可以傾訴,只能跟神說」。多麼諷刺啊!她們竟為那些自己身受其害的罪行請求原諒。



狄厄多內(Dieudonné,意為神賜),48 歲,德羅德羅天主教堂的神父。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然而,那些創傷無法被抹去,一直毒害著心靈,隨著時間過去,陰影越來越大,對身心的摧殘也越大。」塞吉醫生這麼說。我問他那些受害者的家庭是否給予這些女孩支持?他說,有些家庭會支持她們,這能幫助她們走出遭性侵後無法避免的羞恥感。但大部分的家庭傾向於將受害者拒於家門之外,讓她們別無選擇只能流離到鄰近的收容營去生活,或甚至去請求強暴者的家人幫助。如若她們唯一的庇護所竟然是和那些顛覆她們人生的人待在一起,該是感到多麼的孤獨和驚恐啊!
因應全球疫情,我在醫院前等候量體溫,並等候放行入內。體溫計壞了,一直都顯示 32 度,如同顯示一具遺體的溫度一般。進入醫院時,我聽到撕心裂肺的哭聲,見到一些婦女,大約十多人,在樓梯上哭號,雙臂朝天高舉,為一名殞落的士兵嚎喪。另一名士兵舉著他的槍,比劃著解釋發生了什麼。可是我的翻譯告訴我他聽到他們說那士兵是自殺死的。


走廊盡頭,那些女人圍在死者身旁;遺體被白色床單裹著,眼睛和嘴都是闔上的,彷彿是沉沉睡去一般。女人們撲倒在遺體上繼續大聲哭號。幾個民兵,死者的友人也加入弔喪,為他們在戰鬥中殞落的朋友悲哭。我無法確知真正的死因。但又有什麼差別呢?這些人失去了他們摯愛之人。
我在健康中心與歐諾琳(Honorine)見面,她四十八歲,是當地人道救援的工作人員,已經在此工作三年。歐諾琳拿出一本筆記,裡頭滿是女孩的名字,她說,每天最少都有五到六位受害者,大多都是未成年少女,其中很多前來求助的都已懷孕。許多女子都是遭到她們的丈夫家暴。歐諾琳解釋說在這些收容營裡,人們會鼓勵遭性侵的婦女到健康中心來接受治療照護。這裡的醫療結構提供健康評估,並且提供避孕、照料遭強暴懷孕、以及性病尤其是愛滋病的防治。當我們沿著長廊一邊走著時,我看見一間滿滿地有十五位孕婦的候診室,她們等待讓這裡唯一的一位助產婦看診。
我問歐諾琳為何有這麼多的性暴力事件。她與尚-克勞醫生的看法一致,認為強暴是男人們展現他們的能力/權力並報復人生的殘酷的一種方法。對那些民兵而言,強暴當然是一種剝奪當地人民權力的手段,在強暴當地女性的同時,玷汙那些男性的尊嚴。我思索著女性的身體在此成為這種報復行動的受體。許多遭性侵的婦女後來都由於這些暴行帶來的恥辱,而遭受更多的暴力對待。許多人都被逐出原生的社群。

恩札樂(Nzale),30 歲,靠在歐諾琳的腿上。歐諾琳,48 歲,是負責為性侵受害者提供初步醫療並給予她們心理支持的照護員。恩札樂是在為她的七個孩子採買食物的路上遭幾個叛軍強暴,她拿不出那些逞兇者向她索要的錢財。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我再次來到大十字架這裡。這一回,除了右腳以外,耶穌雕像連兩隻手臂也缺了。我的翻譯阿爾豐茲(Alphonse)告訴我,截斷雕像兩上肢,是刻意的,目的是為了讓群眾明白雕像流下的液體不是血,而是雕像內部結構生鏽和著雨水流下來。我問神父對流血的耶穌像和受此吸引的群眾之看法如何,他回答說這種迷信對於這個社區是很危險的,他打算結束這種場面。在禮拜天彌撒時,教堂裡聚滿了專心聆聽的教區信眾,神父警醒群眾錯誤的信仰和迷信帶來的負面效應。可是在外頭,圍繞著十字架聚集的群眾似乎並不理會這種理性思考。之後,當我再次經過大十字架前時,殘缺而流血的耶穌像已經不見,圍繞的群眾也不復見。
我返回健康中心與葛希安(Gracian)見面;葛希安是助產婦,52 歲,從 2010 年就在此工作。在一間有著藍色牆壁的陰暗房間裡,她坐在一張堆滿紙張、文件和檔案的辦公桌前,光線從小小的窗子透進,照在她侷促狹小的工作區域,她逐一叫喚那些準媽媽們。我和她談論她照顧的那些流離失所的孕婦們,問她「對這些婦女而言最緊急迫切的問題是什麼?」她告訴我,現在她們最亟需的是食物和衣服。她們大多數人都只有一套衣服——穿在身上那套,而她們懷孕後,衣服當然不再合身。她們吃得不好,甚至完全沒有得吃,因此,都生下營養不良的嬰兒。
她們坐在那,靜靜的聆聽,不動,也不做什麼。其中兩位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力,因為以孕婦而言她們看來極為年幼。無法確知誰是遭性侵而有孕。

我睡在一間空房,有細薄的蚊帳保護我。父親離世已兩年又十一天,這些日子以來,我每每在夢中見到他或和他說話。今夜,在絲絨般的天空中,月亮如此碩大,似乎懸得比平常更低些。收容營中靜悄悄的,就在我入睡之際,父親來了,輕輕地搖醒我。「爸,你怎麼在這?你不是死了嗎?」我問。他回答道:「是,我是死了。來,我們去散步。」於是我們在滿月的月光下泥濘的小徑上走著,父親跟我敘話,我問了他一些問題,問他是否高興?他說是。他要我寫日記,寫下我每日的所有想法。「可是,為什麼呢?爸。」他從口袋拿出一個小本子,翻著,然後給我看他的筆記,和上頭潦草寫的日常待辦事項:「妳記得這個嗎?」「是的,我記得」我回他。早晨,我因他在我耳旁的輕語而醒來,發現他已離去。剛醒時我好困惑,感覺像是被濃霧環繞,就像覆於伊土里地平線上的那種濃霧。我想到自己即便在父親死後仍然從對他的回憶中得到保護,而事實上剛果的數千婦女卻永遠不可能有這種被保護的感覺。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
一所位於尼茲收容營的醫院,婦女和孩童在這裡獲得照料。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在德羅德羅的健康中心,孕婦們等候接受治療時,都坐在我預先靠著牆放置的那張椅子上。她們說話時,都找點小事,一邊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那個穿著黑衣藍裙的女孩,搔著自己的手背。在藍色牆壁的昏暗檢驗室中,最顯眼的細節,是妝點著這些女性孱弱身軀的彩色配件:一件綠色的裙子、一個玫瑰色的手環、一條紅色的披巾、一枚蝴蝶胸針、一串有藍色珠墜的長項鍊。她們並不直接地與我目光相對,但我看見她們,且我記得她們每個人的這所有細節,我的相機也記得。
剛到德羅德羅時,我擔心婦女們會躲著我,但是今天,我很訝異她們來見我,跟我述說她們的故事;她們知道我是攝影師,而不是人道救援的工作人員。大多數的受害者都由於那完全不在她們掌控之內的性侵恐怖經驗而活在羞恥感和罪惡感中。然而,卻不能將這些婦女和少女們全都歸類為同一狀況。即使集體暴力如此常見,暴力的共同經驗也無法抹滅其對個人的衝擊。她們每個人都值得被傾聽。


諾拉.阿利法(Noella Alifwa)與她在「婦女團結求和平與全方位發展」廣播電台的同事們到此,不止是為了聽取故事,也是為了運用這些素材讓民眾關心這個議題。諾拉和一群女性大約從二十一年前就都在此地的一個廣播電台工作。她們共同成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探討性暴力的問題。諾拉告訴我,她們的組織有四大目標:1) 讓婦女熟知她們的權利;2) 致力於創造平安的社區,讓婦女有安全感;3) 訴求更好的領袖;4) 教導婦女自己照顧自己,不止是遭性侵後第一時間的處置,還有展望更長遠的未來。她們的非政府組織每年照顧超過五十個性侵害案件,同時繼續不斷伸出援手提供協助。她們知道改變並非一朝一夕,她們明白由於文化脈絡將女性視為物件,而且由於缺乏一個可信賴的司法系統,改革的道路必將漫長,且需時時經營。可是,我仍忍不住想起這個女人盛怒打斷無國界醫生組織針對性病以及因強暴造成的懷孕所做的宣導,她認為這些宣導褻瀆神明且偏差。我不能怪她。因為,信仰是如此根深柢固,同時也如此礙事,需要時間和努力才能抹去。
我最後一次經過那個大十字架前面,耶穌像又重回十字架頂,它不再流血了,不過之前被截開的上肢重裝得很笨拙。這回,四周沒有群眾聚集了。

在往羅霍收容營的路上,這是人們可以去取水的唯一道路。
© Newsha Tavakolian / Magnum Photos再次回到那蜿蜒的道路,女人們沿著小徑走,她們的身體因為沉重的水罐和她們搬運到田裡的大綑柴火而顯得沉甸甸。她們大部分都穿著五顏六色的傳統服飾並妝點有三月八日國際婦權日字樣。
我一邊觀察著她們的辛勤和她們的活力,想著是否有一天這套婦女日的袍子將不再是她們唯一擁有的衣服,是否有一天她們能夠意識到這一天的意義,並且真能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