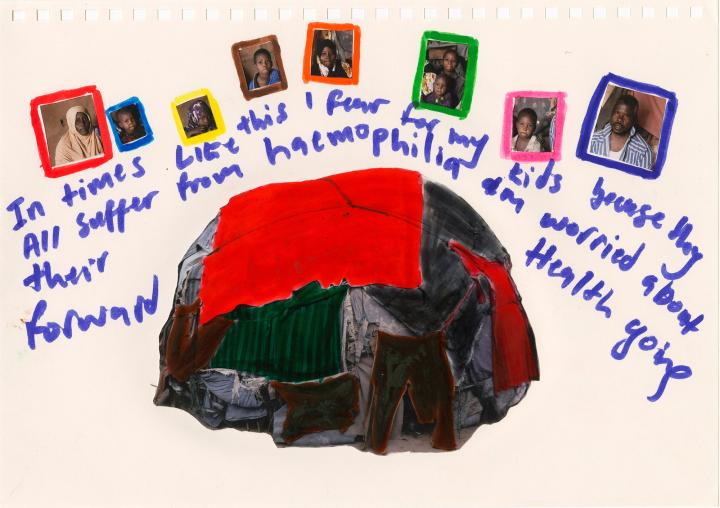劫後餘生:難民與流民

盧安達難民穿過靠近他們母國邊界的坦尚尼亞恩加拉(Ngara)難民營。1994年,坦尚尼亞。
© Gilles Peress/ Magnum Photos暴力衝突爆發時,生存本能驅使人們逃往鄰近的地區或國家。然而,他們避難之地並非總是準備好迎接大量的外來者,因此所有人都必須迅速行動,張羅非正式營地的生活起居。 人道工作者就算不在難民營現場,也會在緊急情況發生的初期趕到,而攝影師亦然。雖然生活條件艱難且相當受限,但關鍵是要維護或恢復那些發現自己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被扣為人質者的尊嚴。
在營地中找尋避難處
逃離一場危機局勢首先要將一切拋在腦後。一旦人們抵達更安全的地方,就必須立即滿足他們的生存需求——建造庇護設施並提供食物、水和基本的衛生服務。對於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已失去一切的人們來說,醫療工作者和人道救援人員可以帶來一線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常生活和相互支持將有助於恢復部分常態,攝影師的鏡頭則捕捉到了這些常態。

1975年,柬埔寨。
© Hiroji Kubota/ Magnum Photos1970年代,柬埔寨與越南的高壓政權迫使100萬人逃往鄰國泰國。這是MSF第一次在難民營工作。在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下,MSF的工作人員在亞藍(Aranyaprathet)和班維奈(Ban-Vinai)營地工作,後來又在非正式的南瑤(Nam Yao)和虔功(Chieng-Kong)營地工作;數年後,後兩者成為正式營地。醫生被派往這些有許多難民定居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沒有用水或衛廁設施,居住環境極為擁擠。
1976 年,克勞德·瑪陸黑(Claude Malhuret)在收容了 7,000 名難民的亞藍營地工作,他說,「沒有人真正了解難民營」「沒有關於這個主題的醫學理論,沒有文獻,也沒有可以依循的定義。我看到這些男人、女人和他們的孩子。當我聽他們講話時,我逐漸了解紅色高棉(Khmer Rouge)政權的恐怖程度。這些人是被追殺的人,他們形容枯槁,四肢因腳氣病(維生素 B1 缺乏)而腫脹。你得引導他們把話說出來,大多數人都受到恐嚇。他們崩潰、啜泣,或至少會感到懷疑。」

1980年,泰國。
© Steve McCurry/ Magnum Photos面對泰國營地缺乏物資和工作人員,又想滿足難民的需要,MSF意識到需要一個穩固、有系統的組織,並以後勤系統作為後盾。在 1977年從泰國回來後,瑪陸黑就強調了這一點。「現今和未來的世界,將會是難民的世界。」他說,「MSF必須為其工作人員提供能有效應對這一新現實所需的資源。」在藥師雅克·皮內爾(Jacques Pinel)的帶領下,MSF在薩凱奧(Sakéo)和考伊當(Khao I Dang)營地建立了一個後勤組織。
MSF人員與難民一起工作,試圖重整營地的生活。許多難民扮演了積極角色,成為護理師、護理助理員和勤務員。1979 年在蘇林(Surin)難民營工作的MSF醫生艾斯梅拉達·盧喬利 (Esméralda Luciolli)解釋:「他們負責監督醫療服務,登記新病人,並將病情最嚴重的人轉診到醫院。這些『衛生守護者』成功了,組織起團隊收集垃圾、教婦女燒開水,以及教孩子上廁所。」

MSF醫生伊夫·科耶特(Yves Coyette)在考伊當難民營治療生病的嬰兒。1984年,泰國。
© Burt Glinn/ Magnum Photos羅尼·布勞曼(Rony Brauman)的第一個任務也是在泰國的營地。1979 年 10 月,他抵達柬埔寨北部邊境的他普里(Ta Prik),那裡有 30,000 名難民剛剛越境。「我們在現場見證了我一生中看過最可怕的事件,」他說。「數以萬計一動也不動的人,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一大群黑暗、擠在一起的人群,在稀樹草原的這個角落裡蜷縮成一團。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嬰兒的哭聲。只有喘息聲、咳嗽聲、風的沙沙聲,以及遠方動物的壓抑叫聲。」
因為救援人員仍然無法越過邊界,只有倖存者能到達此地。援助無法進入柬埔寨,這使得一些人員必須盡可能接近需要的地方以提供援助,而非留在外圍。 因此,1980年2月,MSF與國際媒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一起在泰國和柬埔寨邊境的橋上舉行了一次象徵性的遊行。
他們呼籲允許食物車隊進入該國。瑪陸黑在來自世界各地的攝影機前講話。「此時此刻,50萬名柬埔寨難民, 50萬名平民沿著邊界聚集,可能一天又一天地被送回去面對會向他們開槍的士兵。我們在這裡要求保護這些平民的生命,這些手無寸鐵的人的生命。我們在此懇求你們在我們面前的士兵們,讓這些運送食物和藥品的卡車,讓那些來幫助這久活於悲劇的倖存者的醫生團隊,進入柬埔寨的領土。我們的代表團就坐在幾公尺外,代表著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他們因為經歷了邊界另一邊正發生的事情而驚駭。代表團願意花一整天等待你們的回應和授權。」
不出所料,柬埔寨政權將他們拒於門外。儘管失敗了,重大的媒體報導仍有助於喚醒大眾對難民困境的認識。
幾年後,在1994年和1996年,暴力浪潮震撼了非洲中部,卻與攝影機和全球的電視螢幕距離遙遠。為了拍攝紀錄片《非洲,你痛苦嗎?》(Afriques: comment ça va la douleur?),攝影師雷蒙·德帕東(Raymond Depardon)花了5個月的時間交叉穿越非洲大陸,從南非的好望角再到埃及的亞歷山卓,標題指的是查德革命者在非洲長期停留期間經常喊出的一句話,「痛苦」這個詞在這裡被輕描淡寫地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拍攝的影像搭配著創作者自己朗讀出的簡短文字,這些文字並非實況報導,但它們捕捉了德帕東如何看待和理解每個事件的脈絡。在旅途中,德帕東在蒲隆地遇到了MSF團隊,蒲隆地當時被內戰撕裂。他拍攝了住在帳篷裡和無法取得重要維生物資的流離失所家庭。MSF在營地工作,治療營養不良和由不健康生活條件及食物不足引起的疾病;組織也在不同的省份支援轉診醫院運作。


即使在最悲慘的情況下,德帕東也選擇讓圖像說話。「我不環遊世界,我不為此拍照,」他說。「我設法拍了幾張效果很強的照片,但我和其他人一樣地工作。有時我很害怕,但有時我的挑戰是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一邊是好人,另一邊是壞人。你必須要小心。而有時,你只需坐下來休息一下,照片也可以給我們一些新的方向。」
人的尊嚴是攝影師工作的核心。

將庫德族難民從敘利亞東北部運送到伊拉克庫德斯坦多胡克(Dohuk)省巴爾達拉什(Bardarash)營地的專車。這張照片是2019年在伊拉克薩赫拉(Sahela)邊境哨所拍攝的。
© Moises Saman/ Magnum Photos軍事攻勢和其他暴力事件繼續迫使人們外逃。在近期的2019年,土耳其軍隊轟炸了位於敘利亞東北部土耳其邊境的敘利亞庫德族飛地羅賈瓦(Rojava)。結果造成超過12,000名難民抵達伊拉克庫德斯坦。
「在敘利亞東北部的戰鬥開始後,我們立即對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的入境點進行了快速評估,包括可能接收難民的接待站和營地,」MSF巴爾達拉什專案統籌馬利烏斯·馬丁內利(Marius Martinelli)解釋;巴爾達拉什正是難民定居的營地。攝影師摩西·薩曼(Moises Saman)從一開始就在那裡。
精神健康護理是難民最迫切的需要。MSF精神健康經理布魯諾·普拉達爾(Bruno Pradal)說:「從第一天開始,我們精神健康護理團隊篩檢的大部分人,都表現出焦慮和憂鬱的徵狀。」


來自該地區的醫護工作者組成行動小組,拜訪各帳篷並與家戶會面、識別症狀並提供初步的心理支持。MSF社區醫護工作者和口譯員賈馬爾(Jamal)及賈拉勒(Jalal)在2014 年伊斯蘭國組織占領他們的地區時,都經歷了難民生活的痛苦經歷。「我們逃到了山區,」賈拉勒說。 「我們和我的一些親戚一起越過敘利亞邊境,前往伊拉克庫德斯坦的多胡克。」 賈馬爾補充:「我們曾經當過難民,知道這些人的感受,因為我們有過類似的經歷。我現在的工作是拜訪帳篷與家戶會面,辨識心理創傷的症狀,好讓他們接受治療。」在帳篷之間與群山環抱中,攝影師摩西·薩曼記錄了營地中孩子們尋求的自由時刻。

孩子們在巴爾達拉什營地踢足球。2019年,伊拉克。
© Moises Saman/ Magnum Photos一般會認為,難民在營地中能得到一定的安全措施,但並不總是如此。 與流離失所者和難民合作,需要配合各地當局施加的正式和非正式限制。當各種條件無法再被接受時,你就必須離開。
援助的限制

在盧安達邊境附近的坦尚尼亞恩加拉(Ngara)地區,一個孩子直視正在記錄盧安達難民營內情況的攝影師。1994年,坦尚尼亞。
© Gilles Peress/ Magnum Photos1994年4月6日,載著盧安達總統的飛機在接近首都吉佳利(Kigali)時被擊落。接下來的日子裡,對圖西(Tutsi)少數民族的屠殺開始了。1994 年4月至6月間,有50萬至100萬圖西族人成為系統性滅絕的受害者。這場種族滅絕是政治軍事極端份子實施的長期策略的後果,他們激起了對圖西少數民族的種族仇恨。在此期間,同一批極端份子還殺害了許多反對大屠殺的盧安達胡圖(Hutu)人。1994年4月13日,一支包括尚埃爾韋·布拉多(Jean-Hervé Bradol)在內的MSF經驗豐富5人小組,抵達盧安達首都吉佳利,以支援自1993年以來一直在那裡工作的團隊。布拉多描述了他抵達時的難以置信。「死者比傷者還多,」他說。「但人們使用的武器大砍刀,不能被視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圖西人、被懷疑沒有支持兇手的胡圖人的系統性殺戮最終使我們相信,只有壓倒性的政治決斷才能產生這種結果。」

靠近盧安達邊境城市戈馬(Goma)的一堆大砍刀,1994年攝於薩伊(現剛果民主共和國)。
© Gilles Peress/ Magnum Photos在記錄波士尼亞種族清洗的恐怖之後,馬格蘭攝影師吉爾斯·佩雷斯(Gilles Peress)在種族滅絕發生期間前往盧安達。「這種罪行的嚴重性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西方和已開發國家冷漠的態度,他們本可干預及阻止罪行。」因此,他將他 1995 年的書命名為「沉默」,指的是國際社會的沉默。這本書是他在當地產出的作品合輯。記者菲利普·古列維奇(Philip Gourevitch)是《巴黎評論》的盧安達特派員。談到佩雷斯的照片,他寫道:「你在吉爾斯的照片中所看到的,只因為吉爾斯拍了它而存在,以及因為你正在看著它。那時的一切,只以記憶的形式留下來。這就是生命,也是生命的聲音。盧安達充滿了聲音,而這些聲音中充滿了記憶。」

在卡布加伊(Kabgayi)一處營地附近的醫院,一名面部受重傷的男子看著鏡頭。盧安達,1994年。
© Gilles Peress/ Magnum Photos盧安達的國際人員無法保護在當地僱用的工作人員和病患免於大屠殺,他們知道這些當地人身處危險。當特派小組被疏散到鄰國蒲隆地時,盧安達籍的工作人員在邊境被拒於門外。返回巴黎後,MSF盧安達專案經理尚埃爾韋·布拉多講述了發生中的暴行。MSF決定直言不諱,組織舉行了一次記者會,其聲明發表於1994年6月18日的《法國世界報》(Le Monde)上。「我們是這件事的直接見證人,」聲明寫道。「被殺害人員的名單經過精心準備,並在第一天分發。人們在指揮下被殺,挨家挨戶進行『清洗』。我們知道大屠殺的兇手是誰:由過世獨裁者的隨從人員所領導的民兵。在聯合國秘書長承認種族滅絕正在發生之後,聯合國安理會也承認了。今天,無法引起行動的言論令人憎恨。對付種族滅絕需要一個極端的、立即的應對。目前為止所有的反應只能視為急救,但醫生無法停止種族滅絕!」為了決定是否打破人道中立原則MSF進行了內部激辯,隨後呼籲國際武裝介入。法國軍隊的綠松石行動(Opération Turquoise)能挽救生命,但也為盧安達武裝部隊逃往薩伊開了方便之門。
數十萬盧安達人同時在官方宣傳的威脅和影響,以及對民兵暴行的恐懼下逃離。他們最終抵達在坦尚尼亞和薩伊的營地,人道工作者在那裡為他們提供照護。


1994年夏天,MSF在薩伊組織了一場對抗難民霍亂疫情的應對行動。一旦疫情受到控制,工作人員就要面對(前盧安達軍隊)領導者們對營地居民的殘酷控制。其中一些難民營被改造成奪回盧安達的後方基地;大量援助物資被劫持,難民則受到威脅和虐待。
人道工作者對這種情況感到憤怒,但在如何解決問題上意見分歧。有些人認為MSF應該結束在營地的活動,有些人相信他們仍有機會改善情況,而還有些人則希望MSF無論情況如何,只要難民仍需要援助就留下。1994年11月,在薩伊基伍(Kivu)多個難民營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呼籲聯合國安理會部署一支國際警察部隊,將難民與須對種族滅絕負責的人分開,但沒有得到回應。那時,在努力制定共同應對措施的過程中,MSF面臨了以下問題:組織是否應繼續在營地工作,從而加強種族滅絕者對營內民眾的控制;或者撤出,拋棄其援助遇險人群的承諾?緊急時期結束後,由於情況沒有改善,MSF決定停止在那的工作,並於1994年至1995年間離開各難民營。

盧安達難民穿越靠近盧安達邊境的坦尚尼亞恩加拉(Ngara)地區的一處營地。1994年,坦尚尼亞。
© Gilles Peress/ Magnum Photos留出空間,傾聽並嘗試理解複雜性

尚·高米(Jean Gaumy)照片的接觸印樣,呈現了在梅薩格蘭德(Mesa Grande)營地的難民和MSF工作人員的樣貌。1985年,宏都拉斯。
© Jean Gaumy/ Magnum Photos1980年代的中美洲,特別是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等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游擊隊戰士反抗威權政府,導致內戰。那些沒有受困的民眾逃到鄰國,進入巨大的非正式營地,或在收容社區中生活。超過 15,000 名薩爾瓦多難民聚集在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之間長達200公里的邊界線上。1980年7月,MSF 開始在宏都拉斯的梅薩格蘭德營地工作,該營地距離邊境約50公里。這支由3名醫生和2名護理師組成的MSF小組,首先在有難民躲藏的周邊村莊組織起行動診所,許多因薩爾瓦多的經歷而受到創傷的難民躲在這些村莊裡。在衛生中心裡,該團隊治療患者因悲慘生活條件所引起的疾病。該設施後來成為一間有4個房間的小型醫院,其中包括一間產科病房。

MSF人員在梅薩格蘭德難民營內工作。1985年,宏都拉斯。
© Jean Gaumy/ Magnum Photos
另一張尚·高米(Jean Gaumy)照片的接觸印樣,呈現了卡耶雷雅爾(Calle Real)營地的難民和MSF人員。1985年,薩爾瓦多。
© Jean Gaumy/ Magnum Photos1984年,MSF即將離任的主席澤維爾·艾曼紐利(Xavier Emmanuelli)訪問了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和瓜地馬拉的專案。他帶著馬格蘭通訊社的記者克勞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和年輕的攝影師尚·高米(Jean Gaumy)同行。艾曼紐利想要了解當時MSF以外其他人的觀點。近 40 年後,他仍然相信攝影師的敘述很重要,因為只有主觀圖像才能傳達人道使命的人性面向。「尚·高米明白這一點!」他說。「一旦他完成了我們的任務,他就回去了,他自己付錢,完成他開始的工作。尚有他自己的視覺敘事方式,他的影像能捕捉到一個完整的瞬間。無論發生了什麼,無論發生在何處,我們都能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人類行為的準則,那是因為尚對他拍攝的人有感情。他對世界的觀點是投入的、堅定的。」

孩子們在梅薩格蘭德難民營內玩耍。1985年,宏都拉斯。
© Jean Gaumy/ Magnum Photos高米記得這項工作對他的職業生涯有多麼重要。「這次旅行是一個開始,」他說。「我發現了一些事情。我遇到了MSF的工作人員,他們解釋了那裡發生的事情。他們的故事傳達出他們做選擇的勇氣,每一次任務都改變了我們。攝影師和人道工作者一樣,在我們所看到的危機現實之前,我們什麼都不是,我們不知所措,而這就是讓我們回歸人道的原因。」

一位阿爾巴尼亞科索沃婦女抱著一個孩子。1999年,科索沃。
© Cristina Garcia Rodero/ Magnum Photos幾年後的1999年,隨著阿爾巴尼亞人持續在科索沃遭受暴行,攝影師克里斯蒂娜·加西亞·羅德洛(Cristina Garcia Rodero)前往當地加入科索沃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當我聽說阿爾巴尼亞裔科索沃人被驅逐出他們的國家時,我在墨西哥,但我立即前往當地,」她說。「我知道史高比耶(Skopje)在哪裡、邊界在哪裡,然後我就去了。接著我就得進入難民營和人們交談。」

聚在一起的阿爾巴尼亞裔科索沃難民。1999年,阿爾巴尼亞。
© Cristina Garcia Rodero/ Magnum Photos人道援助工作者那時也在科索沃。1998 年,MSF在科索沃的緊急專案統籌基思·烏塞爾(Keith Ursel)針對在當地開展工作的困難,以及流離失所者面臨的危急情況發出警告。「這些人正承受巨大的痛苦,」他說。「不僅沒有藥物可以幫助他們,現在甚至連那些照顧他們的人也成了攻擊目標。冬天來了,科索沃的氣溫下降到危險等級。大約有 20 萬人被迫流離失所,上千人在森林裡討生活,幾乎得不到任何幫助。」
在科索沃戰爭的停戰談判失敗後,北約發起了盟軍行動(Operation Allied Forces)。空襲開始了,MSF撤離該國,但繼續在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現名北馬其頓)和蒙特內哥羅境內的難民營工作。
在1999年4月1日的新聞稿中,MSF宣布:「今天早上,一架 DC-8 離開比利時奧斯坦德(Ostend)前往阿爾巴尼亞地拉那(Tirana),另一架飛機離開阿姆斯特丹前往馬其頓的史高比耶。他們攜帶了50噸醫療設備和物資、毛毯、帳篷和塑膠布、儲水容器和馬達。4名工作人員在飛往史高比耶的飛機上,另有3人在飛往地拉那的飛機上,他們要去支援已經在當地現場的團隊。」

孩子們在斯滕科維奇(Stenkovac)難民營安慰他們受傷的朋友。1999年,馬其頓。
© Cristina Garcia Rodero/ Magnum Photos「孩子們在玩耍,這表明人類有能力適應他們所生活的可怕環境,」羅德洛說。「他們跟著我,想要玩耍。無論我走到哪裡,他們都跟著我,逗我。小男孩受傷了——你在照片中可以看到孩子們在安慰他。他的朋友年紀也都很小,當他們把手伸出窗外向我揮手時,最小的那個把自己弄傷了。其他人對他都很溫柔,因為他哭了而安慰他。」透過這次讓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任務,她開始更具體地理解攝影師作品的含義。「你必須分享且想要講故事。作品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想去哪裡,以及你為什麼要去那裡。你打算怎麼處理你的作品?你的使命是什麼?你的目標是什麼?你必須去找尋,耐心地找尋。如果你沒有找到你要找的東西,你必須年復一年地再回來,你不能氣餒。這就是你完全無法想像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自2017年8月以來,數十萬羅興亞人成為暴力的受害者,逃離了緬甸前往鄰國孟加拉。薩曼解釋說:「在到達陸地之前,」「大多數難民在泥濘的淺灘上下船,然後帶著他們能夠隨身攜帶的少數物品,涉水穿過植被。」
一位49歲的父親告訴MSF:「我和家人一起逃離我們的房子,但我兒子在奔跑時被槍殺。我把他帶到孟加拉這裡的醫院,但我不得不把我的家人留在緬甸的森林裡,那裡沒有躲避處,只能四處躲藏。我有好幾天沒收到他們的消息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真的很絕望。」
大多數家庭在科克斯巴扎爾(Cox’s Bazar)的臨時營地落腳,沒有住所、食物、飲用水或廁所。MSF和其他組織在緊急情況下設立的醫療設施,很快就不堪重負。MSF醫師康斯坦丁·漢克(Konstantin Hanke)也在場。「515,000(難民)看起來可能是很抽象的數字,但作為身在此地的醫生,你明白這實際上是什麼意思,」他說。「運氣再差一點的話,我們就要面對流行病的爆發。」

在庫圖巴朗(Kutupalong)難民營的MSF診所,一位羅興亞難民和她生病的孩子一起坐著。2017年,孟加拉。
© Moises Saman/ Magnum Photos在造訪了科克斯巴扎爾的難民營後,MSF國際主席廖滿嫦在聯合國難民署的會議上發表談話。「除非親眼看到,否則便很難理解危機的嚴重程度,」她說。「難民落腳點的狀態非常不穩定,看起來就像是用泥巴和塑膠布搭成的臨時避難所,用竹子固定在一起,散落在小山頂上……我們不能忘記羅興亞人流離失所的根本原因,這是緬甸正在發生的危機。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逃離家園,他們會離開是因為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別無選擇。成千上萬的人仍然被困在緬甸,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且他們取得人道援助的管道目前已被切斷。」
MSF在孟加拉難民營進行的調查估計,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間,緬甸若開(Rakhine)邦至少有9,000名羅興亞人死亡。時任MSF醫療總監的王雪梨(Sidney Wong)解釋:「我們與緬甸境內暴行的倖存者見面、做訪談,我們揭露的情況令人震驚,無論是回報家中有一位成員因暴行而死亡的人數,還是他們說這些親人被殺或嚴重傷害的可怕方式。死亡人數的高峰與緬甸安全部隊在8月最後一週發動的最新一波『清理行動」一致。」 報告的結論沒有什麼爭論空間:羅興亞人在緬甸就是被蓄意虐待的目標。
回想起事發數週後的旅行,薩曼想起了他所目睹的一切。他說:「總體而言,我看到的是最脆弱的人們——老年男女、兒童,以及無人陪伴的年輕媽媽和他們的孩子——這在我的腦海中產生了共鳴,但一個反覆出現的想法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即使在世界不同地區親眼目睹了類似的危機之後,在理解身為難民是怎樣的感覺上,這些經歷也完全沒有參考意義。」

衣索比亞難民準備登上將他們從哈夏巴(al-Hashaba)中轉營轉移到烏姆·拉庫巴(Um Rakuba)難民營的巴士。2020年,蘇丹。
© Thomas Dworzak/ Magnum Photos即使在今天,暴力事件的爆發仍迫使各大洲的不同族群集體逃離家園——超過 8,000 萬人被迫流離失所或成為難民。出乎意料,其中有73%的人是在鄰國避難。在蘇丹的衣索比亞難民說明了這一點。2020年11月上旬,衣索比亞北部的提格雷(Tigray)地區爆發了當地武裝部隊與中央政府軍隊間的戰鬥。約 60,000 人在邊界的另一邊尋找避難所,另有數十萬人在提格雷境內流離失所。在第一批難民抵達後,MSF就在蘇丹展開工作,提供支援和醫療援助。12 月,攝影師湯瑪斯·德弗札克(Thomas Dworzak)前往加達里夫(al-Gedaref)地區加入難民。難民潮湧入並非首次,在1985年的人道危機期間,就有大批衣索比亞難民抵達此地。30 年後的現在,該地區過去的難民營已變成社區,生活在那裡的衣索比亞人也已融入了社會。

衣索比亞難民入境點哈夏巴(al-Hashaba)村的落日餘暉。2020年,蘇丹。
© Thomas Dworzak/ Magnum Photos